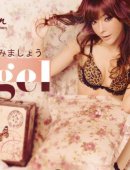-
存在与虚无:韩国艺术家金佶煦作品展(3)
- 发表时间:2018-09-02 19:37 | 巴黎女士女性时尚网 | 点击数: 次
-
大奶女
胡一天工作室声明
成都市区现巨响
戏弄巧心
344944.com
安娜霍兹
夏目奈奈种子
吉他在线调音器
毕升升
青纱帐边的女人
-
“秘密花园”系列作品的创作过程,可以视为金佶煦以追寻童年经验为线索,在观照普遍性的怀乡情绪的基础上,经由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象征性表达,进而重新审视自我和他者之间的意义关联性,通过他观和自观的双重观看,最后进入对于人生的终极意义的思考。
在这之后,金佶煦的创作进入到了一个更为自由和广泛的境界。
其后所创作的“刻痕”系列在金佶煦的思维逻辑中可以看作是“秘密花园”系列的一个延续,通过“思维之手”、“贤哲”、“英雄”这几个子系列的作品,他重新思考了精神与物质、瞬间与永恒、高尚与平凡这些普遍性的概念组合,从而颠覆了人类的知识史和精神史的传统。就像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所宣称的那样,“一声断喝——上帝死了”,打破一切固有的概念限制,“重新评定一切”,一切都可以重新命名。
而在近几年的创作中,金佶煦的创作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他的作品不再是单纯的黑色,而是在黑色基调中又有了一些色彩的象征性,其中尤以金色和银白色最为普遍,就像交响曲中的铜管和木管的音色,它们的出现总是昭示着一种希望和信心。另一方面,在最近这几年的画面中,他表现出了对于线条的表现力的浓厚兴趣。他把自己的这部分创作称之为“用油画的方式来画的水墨画”。这个动机来自于一个有趣的故事,金佶煦在韩国结识了一个来自中国西藏的贤哲,这个贤哲告诉他,在敦煌的一个唐朝的画工是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的前身,而他的后世将在韩国出现,名字叫金佶煦。这个贤哲进而告诉他,你就是那个金佶煦。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由原来的金东基改为了金佶煦。这个经历,对于一个在十四岁的时候就皈依了的虔诚佛教徒而言,意味着是一次重生。于是,他将自己假设为是那位唐朝的画工,用绘画的方式践行了精神的苦修。他的画面中对于线的研究和体悟,就是这种精神苦修的结果。他一方面将自己的物质生活简化到一个最原始的状态,另一方面,用高强度的工作来使自己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对于画面中的线的感悟中。最终,他体会到了线是人的本真状态的最直接的表达手段。在符号学的研究中,原始的记号经由符号的意义固化,最终形成了固定的语言表达。这是一个意义的“编码”过程。今天,那些已经高度程式化了的传统水墨画的技法体系和语言逻辑,后人只能在这些已经固化了的程式中去重蹈前人的语言,这是传统水墨画的衰落。金佶煦的信心来自于试图要用油画材料来实现水墨画的变革,就像冥冥中“金佶煦”这个名称注定要和那个无名的唐朝画工发生关系一样,他认为这是命运昭示他必须要完成的一个责任。金佶煦的工作方式是将这些已经固化的语言逻辑进行“解码”,让能指与所指发生分离,这样,线条由语言、符号重新回到记号,进而重新赋予它新的意义和新的自由度。故此,我们可以发现,在金佶煦的这些近作中,线条既和形象有着若即若离的关联,同时,它们又是独立的。线条本身就体现着节奏和韵律。而这种节奏和韵律是和人的心律、气息以及情绪的变化是一致的,一笔而就,直抒心意,不加修饰。进而,他试图使自己的绘画与人的最本质的精神状态和生命意义发生关联。
本次展览,可以视为是金佶煦在2000年以来的所有的艺术探索实验的一个集大成。不管是人生感悟还是艺术观念、技术表达,都是他自身用艺术来苦修和禅悟的一种必然结果。更有意思的是,在这次展览中,他的绘画又出现了由平面向立体的变化。这个变化既有形式语言上的尝试,又有材料观念上的传达。首先,将线条与立体形式相结合,并不是什么立体主义的转换,而是为了进一步解放线条的属性,使之不再具有“由平面塑造立体形式”的假设,这样,就从根本上松动了线条与立体塑形之间的造型编码假设,使线条回到了一种纯粹的精神物化状态。其次,包装箱这个材料运用,还隐喻了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暗示,包装箱就像穿在人身上的衣服一样,它是物质意义上的一个概念,但是在本质上,它又是空无一物。金佶煦以此来象征着一种物质与概念、能指与所指、存在于虚无之间的关系。而这些,仅仅是构成了一个逻辑框架。而在这个框架之上,金佶煦又一次带着我们回到了他的“秘密花园”,线条游走在这些箱体的表面和内部,就像植物漫无目的的生长,它们似花非花,似人非人,又好似在敦煌石窟中的那些飘荡在虚空中的飞天形象。在这里,金佶煦提出了一个简单而又值得深思的问题:难道人的存在比植物更有意义吗?
Tags: 大奶女 胡一天工作室声明 成都市区现巨响 戏弄巧心 344944.com 安娜霍兹 夏目奈奈种子 吉他在线调音器 毕升升 青纱帐边的女人
- 爱美
- 健康
- 情感
- 美体